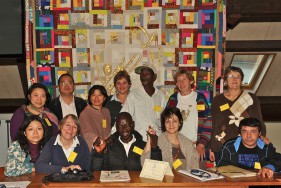Other languages
- Kiswahili
- Malagasy
- Nederlands
- Polski
- Português
- Deutsch
- Italiano
- 繁體中文
- ภาษาไทย
- 简体中文
- Български
- Română
- Magyar
- عربي
持久志願者,另一種生活方式?
持久志願者選擇和貧窮家庭的生命相連結,隨時準備出發到需要他們的地方。截至2014年1月為止,全世界共有400多位長期投身的志願者,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,有著不同的職業、信仰及社會背景, 有些獨身 ,另一些成家。他們分佈在各大洲的30個國家,分享赤貧家庭的日常生活,並投身在許多不同的行動計畫中。 他們不斷以赤貧家庭的生命培訓自己,並日復一日地寫下他們從最被排擠的族群中所學習的一切:讓他們受到傷害的是什麼?讓他們得以前進的又是什麼?這些紀錄建立了第四世界的行動基礎。 持久志願者的主要使命就是團結各階層,務使每個人的尊嚴與權利都能受到尊重。這些志願者透過住所、工作、知識的分享及其他各種行動成為窮人的鄰居、同事、朋友及合作伙伴,見證並記錄窮人的生命、勇氣、思想與盼望,為了將歷史與榮耀還給窮人。一方面跨進貧民窟和赤貧同胞為伍,另一方面積極和盟友與各個領域的夥伴一起合作,努力在地方與國際舞台上,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家庭爭取平等的參與權利,因為唯有創造條件,讓天天與赤貧搏鬥的家庭成為抗貧與發展計畫的主體,極端貧困才能被根除。 所有的志願者不論年資及所擔負的責任為何,都領取同等的生活津貼,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,為了透過簡樸的生活方式,表達與赤貧家庭的團結關懷。
把榮耀還給窮人
華人持久志願者的見證 若瑟.赫忍斯基,這個在近代影響法國與歐洲抗貧運動深遠的法國人說:「窮人是我們思想的導師。」十月十六日,國際消除貧困日的前一天,我終於開始領悟這句話。 那是個涼爽的午後,一個出身貧困且充滿毅力的年輕女孩,領我走到台北的一座橋墩下,那是她出生與成長的地方;她引領我去拜訪那位看著她長大的鄰居,國際根除貧困日的主角。在驅車前往市中心參加國際消滅貧窮日的紀念活動之前,在車水馬龍的快速道路旁,她帶我來到一所亙古以來一直存在,卻從未被承認的學校;在那裡,一如在世界各地的貧困區,我有機會聽到充滿人文深度的一堂課。 替我上課的是一位高齡九十八歲的張伯伯,他既沒有學歷,也沒有地位,但是,他對社會底層的受苦者的認識與關懷無法以學位來衡量。那天, 在一群飛來舞去的蚊子中間,在車聲與狗吠聲中,張伯伯慷慨地為我上了難忘的一課。 其實,我在1991年就已認識張伯伯。但是十多年前,我還聽不懂他的話,不只因為他濃重的湖南口音,更因為我不夠相信他可以教導我生命的功課,所以我一直沒把他的話聽進去。雖然十多年來我一直深信:窮人可以教我許多大學及書本中沒有記載的知識。但是,那信念並沒有深入骨隨;中國「人微言輕」的傳統概念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。在法國國際第四世界總部接受持久志願者訓練時,有多少次我聽這個組織的成員說:「窮人總是盡力扶助比他們更窮困的人。」但是,我就像新約聖經中,那位不相信耶穌已復活的使徒多默一樣,除非親眼看見,親耳聽見,親手去觸摸,否則便不相信。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,是我內在的改變,我從聽不懂窮人,到慢慢聽懂並收獲滿滿的過程。我一方面驚訝於內在深層改變所需的時間是如此漫長,這個改變關係到對窮人的相信;一方面驚訝於窮人所能教導我們的生命功課是如此豐富,過去我浪費了多少學習的機會? 1945年,張伯伯以軍人身份來到台灣,掐指算來,他在台灣六十多個年頭。張伯伯十幾歲就離開湖南老家,她的姪女說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,家人一直找不到他,失望之餘,以為他已離世,就燒紙錢給他。 九年前,也就是離開中國大陸五十二年之後,他再度回到湖南,企圖尋找親人的痕跡,雖無功而返,但他還是不放棄希望地留下字條。後來終於和親人聯繫上,所以他於次年,也就是再度返鄉。 超過半世紀的分離,他的兄長們早已離世,沒見過他面的子姪輩仍然熱烈歡迎他,看到哥哥的女兒,他覺得像看到自己的親女兒一般。這位姪女也馬上把他當成父親般服侍,雖然他們之前從未謀面。2001年之後,早已當上祖母的姪女來回在兩岸間奔波,為的是接他回湖南享天倫之樂。已經耳順的姪女不放心留他一個人在台灣,所以在辦好扶養手續之前,三番兩次到台灣來照顧陪伴他。 在這個沒水沒電的地方,在這個警察威脅要拆除的房子內,她陪張伯伯ㄧ起被蚊子咬,陪他飼養對面市場撿回來的雞,陪他照顧流浪狗中途之家託付的狗。她替他包水餃,擦背;夏季颱風侵襲時,她保護他,打一一九向警察求救。今年三次颱風,社會局安排他們到一個收容中心避難兩回,每次都住了好幾天才又回來。 不久前,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,張伯伯的戶口被朋友遷出來,有一段時間,他成了沒有戶口的遊民,失去了貧民的身份。幸好,認識他多年的里長作保,讓他的戶口寄在一戶里民家,他和姪女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把戶口搞好。一直沒有地址的張伯伯能夠理解一般人的顧忌:「人家不認識你,怎麼會讓你把戶口寄在他那兒?」;但是這種疑慮還是有邏輯不通之處:「寄戶口又不吃人家飯、又不喝人家水,怎麼人家就是不太肯幫這個忙?」 張伯伯常提那個他帶大的小孩,本來是將官,退休之後改做貿易。這孩子小時候常來找張伯伯,因他父母忙得沒空照顧他,所以張伯伯常陪他說話,告訴他一些人生道理,張伯伯觀察到這孩子常羨慕地看著別的孩子買零食,所以總會給他一點零用錢,讓他也可以跟別的孩子一樣,也因此,這個機靈的小男孩每天上學前都會來找張伯伯。 一轉眼,小男孩已步入老年,在社會上有了地位,但他已不願意走到快速道路旁來看當年的張伯伯了,他已不需要兒時那五塊買餅乾的零用錢。張伯伯體諒這個乾兒子也有個八十多歲的老父要照顧,不能常來;而且,二十多年前他曾安排張伯伯就醫切除腫瘤,讓張伯伯銘記在心。但是,張伯伯感到遺憾的是:小時候,這孩子不會把人分為上等人、下等人,長大就不一樣了,發生了什麼事? 張伯伯說:「有錢的人很幸福,颱風的時候都不怕;貧戶的房子一遇到刮風下雨就不能住。」但是,他宅心仁厚,並不將眼光停留在自己的困難中,他繼續說:「有人比我更苦,住在橋下的那對母子,一天只吃一頓飯,我沒錢與他們分享,只能將我們的食物拿去給他們。我心裡痛苦,因為幫不了什麼,我自己住的地點也沒個準,警察曾經威脅要拆除我的房子。還有另一位姓劉的先生,住在橋底下,現在天冷了,他睡覺的地方連墊子也沒有,我就給他準備了小房間。」說到這裡,張伯伯好高興,要我進去看看這個房間,我能感受到他因為幫助了一個比他更苦的人而感到快樂。我好敬佩他,他不但與劉先生分享住的地方,還把鑰匙交給他;他細心地觀察到劉先生連個洗衣、曬衣的地方也沒有,所以與他分享了快速道路旁的曬衣繩。不僅如此,在旁人對劉先生發出不信任的言語時,他替他辯護:「我認識他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,他在橋下快一年了,別人不租房子給他。他白天去工作,晚上回來,也沒跟人吵架,怎麼壞?」 張伯伯和許多處境不利的家庭引領我去思考「教育」這件事,窮困的人似乎不需要,也不等著我們去“教育”他們。相反地,我們能夠從他們身上學習慈悲、仁愛與團結關懷的內涵。張伯伯和我在北美與西歐所遇到的貧窮家庭一樣,他們在靜默中,努力地活出他們所相信的生命價值。我看到他們實實在在的活出友愛與互助的德行,在極度的匱乏中,還是幫助了比他們更苦的人。
生命強於一切
伯爾納德‧高爾 [1](Bernadette Cornuau) 21歲那一年,我發現了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,在那裡有265個家庭被棄置不顧,失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有一個小男孩悄悄地告訴我:「你知道嗎?別人常常嘲笑我媽媽。」我聽了之後心中忿忿不平。 我有幸能夠認識若瑟神父,那時候,他和貧民窟的男人、女人和孩子們,一起對抗赤貧這道銅牆鐵壁。這個人趕在滿佈泥濘與垃圾,不斷接受救濟,而且常有鬥毆發生的地方,種下最美麗的樹木、建立一所圖書館、一間美術沙龍、一座石砌的聚會所,並在牆上飾以知名畫家的作品,這個男人敢在深夜裡寫信給千萬個貧民窟以外的人:「來吧!來向最貧窮的人學習,學習建立一個正義與和平的世界,在哪裡,所有的人都能被肯定、被認識。」我完全同意。 為什麼我被這個運動所吸引?因為生命強過一切,第四世界家庭生活的真相、他們所遭受的痛苦、他們的希望,塑造了我們的奉獻與投身,塑造了這個非政府組織的思想與行動。 [1] 伯爾納德‧高爾-(Bernadette Cornuau)於1960年進入第四世界志願者團體,為了根除貧困,她全職投身已近半個世紀。
划向深處去
創立人談志願者團體 若瑟‧赫忍斯基 一開始,我們只是分享一個單純的意願,以最貧窮的家庭為中心,和他們結合在一起。我們的合一在於每個人都理解到:和最貧窮的家庭結合在一起,卻缺乏彼此間的合一,就失去了意義。赤貧家庭對志願者團體的需要是如此真確與明顯,也因此,這個團體必將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事實。 最早期的志願者都是年輕的女士們,在草創時期,這些志願者必須有很多的愛,甘冒許多的風險,看得很遠,不只猜測這些家庭的痛苦,也推想他們的未來:這些父母及孩子的未來。為了一個充滿想像與希望的未來,必須要馬上接受一些物質上的 成為志願者,從一開始就意味著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赤貧者的手中,同時也是放在和你思考方式迥異的志願者手中。 建立一個包含各種信仰,各種意識形態的志願者團體,是人類最根本的需要,這個需要是一種權利。此外,這也是赤貧者成為所有的宗教與意識形態的核心的權利,是人們儘管不同仍合而為一的權利。 志願者初來乍到的時候,我就應該告訴他們:是輪到他們划向深處的時候了,他們必須出發到其他的貧困區去,他們不能封閉在自己之間、滿足於自己的小團體。划向深處去的意思是:總是住在簡陋的帳棚內,把背迎向所有的風,隨時準備出發到任何地方;划向深處也意味著,各種背景、年齡和各種宗教信仰的人,以赤貧家庭為核心,學習一起生活,互助合作。 摘譯自若瑟‧赫忍斯基所著《窮人即是教會》,頁167-171.
赫忍斯基報告:《極端的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》
1987年2月11日,若瑟‧赫忍斯基以法國社會經濟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此報告,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貧窮的重要參考文件,她在法國及其他許多國家得到了巨大的迴響。這份報告的原則特徵是: 關心窮人的未來,遠觀一個長程的政策,因為緊急的解決辦法只是暫時減輕了貧窮的狀況,但從未消滅貧窮。 推動一個整體的行動,包括最低收入的保證、居住、健康、職業訓練與工作各方面,因為如果僅抓住一個單獨單領域,卻沒有同時在其他領域有所舉措,這種頭痛醫頭,腳痛醫腳的行動與政策注定要失敗。 促進一個以赤貧人口為合作者的研究,認識最貧窮的人,並以合作夥伴看待他們,創造讓窮人表達與參與的條件,因為他們的發言權的缺乏是我們的社會組織最大的缺陷,這導致貧窮的歷史總是與慈善救濟事業相隨並行。 確保窮人在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的權利,沒有這些權利,就沒有公民與政治的自由。 “Chronic poverty and lack of basis security” (report)